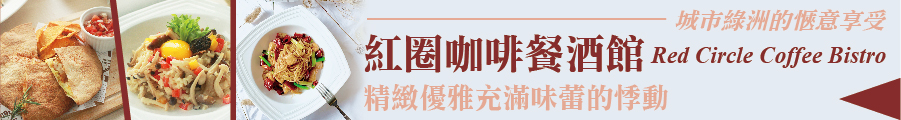《彼岸花》題記:蛇山烈士祠前,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祭
張志奇 2025/09/18 9884
《彼岸花》題記:蛇山烈士祠前,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祭 (詩/張志奇)
蛇山低首,青碑冷,銘刻一九三八年江漢血印。
四省交界,百萬兒女,以骨作城,以血為旌。
六月,倭寇御前定策,把武漢寫進侵略牘;七月,華夏揮師,把鄱陽湖、大別山、長江浪刻在衛國的青簡,亮出抗爭的戟。
三十五萬虎狼沿長江,沿鐵路,沿燃燒的村莊合圍而來;我軍在萬家嶺、田家鎮、信陽關、武勝關一寸一寸把“速戰速決”撕成血帛,飛落江澤。
四十萬傷亡,換二十萬敵魂,第一次把“戰略相持”寫進焦黑的教科頁,亮出希望的炬。
十月二十五,主動撤離,武漢陷落,卻保住時間,保住空間,保住民族屋頂不彎的梁脊。
今我來,蛇山烈士祠前,七月未盡的彼岸花忽然紅得逼人——無葉如戟,花瓣反卷如幟,從石碑燒向天際。
我問花:“可是當年死守武勝關的壯士歸來看故鄉的畦?”
花不言,只把殷紅灑向長江對岸的霓。
風一過,十萬盞小紅燈齊明——照見八十年未冷的血跡,照見八十年未合的寰宇,照見大洋彼岸仍被鄉愁勒緊的漂泊帆影。
於是:彼岸花不是黃泉的招魂幡,而是中華臍帶的絲——一端系蛇山下沉默的碑林,一端牽海外未歸的膝影。
我俯身,折下一瓣猩紅,夾進護照的頁隙;讓它替我作證:
此身所至,紅不褪色,根不漂移;讓蛇山的月光也照見日月潭的紅暈,照見我們終要合璧的同一輪團圓的月。
明月一輪,照徹歸程,不留翳。
注:烈士祠:指蛇山南坡忠烈祠。原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國民革命軍十三師所建表烈祠、抗戰軍興,國民政府將其辟為忠烈祠。抗日戰爭勝利後,湖北省政府在原址重建新祠,將抗日陣亡將士牌位入祀其間。辛亥革命百年重建,左右兩端,分置辛亥革命武昌首義、抗日戰爭武漢會戰之先烈靈位。